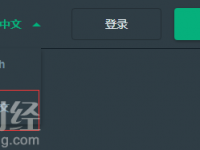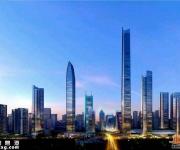深圳,你为什么注定留不住华为
通过压低成本来保持竞争力、从而维持高增长的模式,是一种典型的不可持续的旧经济模式。长期来看,它将使人民的可支配收入(及其背后的内需市场)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低(过去10多年就是这样),最终由于国内需求的不振,不可避免地成为无根之木和无源之水。
(搜狐财经思想库:让思维有乐趣,让思想有力量!汇集顶尖财经智库,分享深刻透彻的调查研究,旨在普及常识,为网友提供思想洞见和专业分析。)
深圳的编年史与硅谷一样年轻,甚至比硅谷更年轻。但相比于金融危机以后依旧一派欣欣向荣的硅谷,深圳的步履却是沉重而蹒跚。
上周,一篇《不要让华为跑了》的网红文章晒出了一份这个中国最年轻的一线城市的病历报告——其实这只是诸多病症之一,而同时出具的诊断书则是似是而非的。
一
不要让华为跑了》一文认为,从目前情势看,华为很可能将自己的终端部门从深圳整体搬迁到临近的东莞,今后甚至不排除将更多其它部门也搬离深圳。其主要原因就在于,深圳高得离谱的土地和房产价格大大增加了华为的生产成本以及华为员工的生活成本。
即便华为公司所处的深圳市龙岗区在情急之下喊出了“服务华为,马上就办!”的口号,并已经采取了一些实际行动,也仍然很难扭转这一大势。雪上加霜的是,近期还有报道说,另一家中国著名的高科技企业中兴通讯也将于今年7月起将它的生产基地陆续从深圳搬迁至河源……
虽然深圳市市长许勤第一时间就两家公司的搬迁作出了“澄清”,但这并不足以改变这样一个残酷事实:长期来看,华为和中兴最多只是将研发和销售部门留在深圳,而对带动地方就业和整个产业链影响最大的生产基地将会无可挽回地跟深圳拜拜。
文章的结论是:实业和地产彻底走向了对立面。而事实上,楼市——以及其他投资市场——泡沫所导致的制造业萎缩恶果不仅在龙岗、在深圳已成为现实,也是今日中国经济的一个缩影。
这不由得令人联想起远在万里之外的中国创业者的朝圣之地——硅谷。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随着美国经济的复苏、特别是苹果、Facebook这些高科技企业近年来的急剧扩张,硅谷现在已是整个美国房价最贵的地方。《福布斯》杂志2014年公布的数据显示,全美房价排名前两位的地区都在硅谷,排名第一的Atherton和排名第二的Los Altos Hills房价的中位数分别高达670万和540万美元。而在过去3年里,整个硅谷地区的房价年均涨幅超过30%,显然不输于北上广深任何一地。
不过,似乎没有哪家重要的企业因此动过搬出硅谷的念头。
道理很简单——即便包括房价在内的商务成本上升得再快,硅谷在全美、甚至在全世界范围内仍然有着无法撼动的牢固优势,这使得硅谷企业的营收、利润和员工薪资水平上升得更快,足以覆盖经营和生活成本的上升。反观深圳,作为昔日中国改革开放的试验田,它的得天独厚的优势正在流失……
二
硅谷是一个随时都能引来滔滔不绝的长篇大论的题材,以至于我觉得在这里说任何关于它的话题,都是多余的。
但心底里,我其实从不期待这类络绎不绝的“创新观光”(一位斯坦福大学负责接待的人士发明的词汇)能够在世界其他地方结出什么果实。相反,我还很怀疑那些拿了纳税人的钱(或大机构的资助)有机会到Facebook公司的免费食堂品尝一顿烤肉的中国走马观花者回到国内后,除了多了一些社交场合的谈资外,丝毫无助于中国的创新事业。甚至,他们身上不自觉地滋生出来的那股洞悉了互联网和创新精髓的自满情绪反而会给真正的创新拖后腿。
每一个人都能轻而易举地从硅谷的成功经验中总结出十条八条金玉良言,但没有人能够否认,相比于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科研实力、政府的财税激励、优越的原材料、丰沛的劳动力以及庞大的市场……杰出的头脑才是我们这个全球化信息时代压倒一切的首要资源。哪个地方最有能力汇聚那些充满聪明才智而又雄心勃勃的人才,它就会自然而然地成为创新中心。而对于真正的人才来说,自由的空气比什么都重要。因此,硅谷精神的核心其实很简单:去管制化。
这就是为什么硅谷近年来遭遇了世界上众多城市——从伦敦到都柏林,从柏林到北京——的挑战而始终屹立不倒的根源。上述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独特优势和机遇,但硅谷得以成为硅谷的根本理由是美国体制——它磁石般地吸引世界各地怀抱着远大理想的精英涌往美国,帮助它成为全球最具创新力的经济体。
两个多月前去世的英特尔公司前首席执行官兼董事长安迪•格罗夫(Andy Grove)被称为“硅谷缔造者”,他是一位出生于匈牙利的犹太人,原名András Gróf。这位典型的外来者脾气火爆、性格偏执,他的名著《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书名就清晰表达了格罗夫的信条。
今天依然如此。尽管硅谷本身是美国风险投资业云集之地,全美每年的风险投资也有将近一半投在了硅谷,但身份“可疑”的俄罗斯数字天空技术(DST)首席执行官尤里•米尔纳却成功地成为了Facebook的大股东(拥有它近10%股份)和Zynga的高级顾问。而在过去10年间,硅谷每10家企业中有4家的创始人或联合创始人是外来移民。与此同时,硅谷的风险基金也频繁地对外投资。投资过携程的著名的红杉资本就不说了,就在去年这个时候,另一家总部也在深圳的中国无人机制造商大疆创新科技有限公司(DJI)还曾获得硅谷风投集团阿塞尔合伙公司的7500万美元投资……
为了挑战制约创新的法律和政策桎梏,硅谷科技业巨头近年来还频繁地将手伸向政治领域。Facebook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创建了一个政治游说组织,目标是促成放宽外籍工程师和熟练技术工人流入美国的移民改革法案;谷歌首席执行官拉里•佩奇曾提出,建设类似于美国内华达州沙漠的火人节(Burning Man)那样的实验营,通过颁布新的法律来促进创新;而风险资本家皮特•泰尔甚至渴望完全脱离麻烦的政府,在海上建设一个“漂移社区”;最近几个月里,谷歌、微软、Facebook、亚马逊、思科、Dropbox、Snapchat和雅虎等15家市值超过2万亿美元的重量级科技公司联手加入苹果公司阵营,支持后者就数据保护和安全与美国政府进行斗争,最终迫使联邦调查局放弃了解锁iPhone的要求……
具体地看,这些努力中的一部分近乎疯狂,并在世界各地政坛和民众中引发了强烈的担忧和反弹。但从宏观上看,这种自发的自由企业文化不正是造就硅谷的土壤吗?当年那些从欧洲来到美国的早期移民们也正是凭借着同样的对未来的憧憬和令人觉得不可思议的奇思妙想缔造了美国规则。
从这个意义上说,硅谷就是当代美国的一个“特区”,只不过与中国的深圳有所不同,它不是哪一个拥有无上权威的老人划的一个圈,而是一群怀揣着各种梦想的各色人等自发地聚在一起的一片没有围墙的开阔地。
三
我们当然不能指望硅谷模式能够在中国得到复制,但在中国既定的制度框架下,我们多少还是能够指望一些东西的。
再过两个多月,深圳特区就将迎来它成立36周年纪念日。这时候,我觉得特别有必要重新审视一下“特区”的真义。
如今,我们时常能耳闻,某个书记或县长、市长、省长为官一方,造福当地,百姓感恩。若仔细审查一下他们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那么最常见的故事便是:他凭借个人的特殊人脉资源从他的上一级政府那里谋求到了一些特殊政策——想象力一般的多半是打税收优惠的主意,而时下最新潮的则是弄到一两项特别的金融市场(或工具)许可证。再有就是引来一些别人很难弄到的资源,特别是中央级项目和集中的资金投入……总之,在眼下的中国,要把一个地方的经济搞上去,仿佛主要是要靠争取被上级允许做一些别的地方不准做的事情。
这就是目前许多地方争办特区的动力所在,换一种更加学术的说法,现在的所谓特区,即通过对某一项(或多项)政策的排他性的垄断,构筑一个对某些社会资源具有特殊诱惑力的高地。
然而,这种画地为牢式的“经济特区”,对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来说是一件有益之事吗?它的功能究竟是对外“辐射”和“带动”还是向内“抽吸”和“攫取”?
我觉得,我们有必要沿着改革开放一路走来的历程回溯到最初的源头,去找回特区未经异化的原初意义。当年邓小平设立经济特区的出发点是十分明确的:在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初期,有些地方在资源条件(比如更接近海外市场的沿海省区)和人们的观念意识方面比全国其他地方更容易接纳和消化一些新的探索、甚至冲击,因此需要靠这些地方的先行尝试来积累经验教训、取得收获和提高,进而带动全国一起发展。至于所谓“特殊政策”,他给的最多的其实只是不轻易说“不准”而已。我记得邓小平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大胆试、大胆闯,试下来不行,大不了再收回来。
因此,在他眼里,特区就是一片单纯的试验田,是一种过渡形态,而且伴有不小的风险,这一点如今已经被许多人忽略和淡忘了。虽然到了上世纪90年代邓小平曾经公开感叹:自己深为没有早一步把上海列为经济特区而后悔,但他当初的这种犹豫在逻辑上是不难理解的——作为承担着全国1/6财政收入的工业基地和经济中心城市,上海如果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搞特区,那会是一个大到几乎无法承受的赌注。而深圳,之前不过是一个蛮荒的边陲小渔村罢了,甚至根本算不上是什么赌注。
只要有这样一片充满新奇机遇的处女地,就一定会有敢冒风险(同时意味着高收益的可能性)的人前去耕耘;成功者多了,就会吸引越来越多的人才和投资流向特区;假以时日,它也就自然而然地变成了一块资源高地。但我认为必须要区分清楚的一点是:当年的特区——最典型的如深圳——之所以成为这种高地,是在风险和不确定中大胆探索的结果;而不像时下的这些特区,是为了有意识地筑起一块这样的高地而人为地设置排他性的政策壁垒。时下的这种特区,不是在为后来者探路,而是在垄断某种特殊利益,它们完全走到了改革开放之初设立特区时的初衷的反面。
这就是深圳所面临的深层压力和挑战。如果仔细看一看龙岗区“服务华为,马上就办!”的具体举措,你就立刻会发现,深圳所能给华为(还有中兴)提供的“服务”,东莞没有一样不能。而且,由于各方面的成本更低,东莞能够提供得更多。而在东莞身后,还有一长串的地方时刻准备以更优惠的成本去抢食深圳、东莞们的地盘。
所以我说,今日中国所谓“特区”与硅谷的距离,就是百度与谷歌的距离——它们或多或少是凭借着特殊的政策垄断垒筑起来的一个个既得利益城堡。当然,这可能怪不得深圳和东莞们。
四
回到我们文章的开头,我还想进一步指出,过去10多年里各级政府深度关切的所谓“商务成本提高”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其实是个伪问题。
撇开复杂的房地产泡沫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我之前在思想库发表过分析文章)不论,试图以压低营商成本或阻止其上升的手段来保持经济竞争力的做法,不仅行不通,而且也是有悖于经济发展根本规律的。
我们发展经济是为什么?说到底不就是为了提高全民的生活水平吗?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了,人民的收入和消费水平提高了,当地的商务成本必然会水涨船高。
要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根本的动力是提高全社会的劳动生产率,这就需要技术、模式及其他各方面的创新。政府的职责便是营造鼓励创新的制度环境,而其中的第一要务就是减少管制。就连一向低调谨慎的任正非在接受采访时不也说了吗——地方政府到底需要什么?“……法治、不干预。其他的交给企业来做。”
通过压低成本来保持竞争力、从而维持高增长的模式,是一种典型的不可持续的旧经济模式。长期来看,它将使人民的可支配收入(及其背后的内需市场)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低(过去10多年就是这样),最终由于国内需求的不振,不可避免地成为无根之木和无源之水。
中国经济当下面对的严峻形势提醒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全社会必须彻底扭转这一错误认识的时候了。
信息首发:深圳,你为什么注定留不住华为